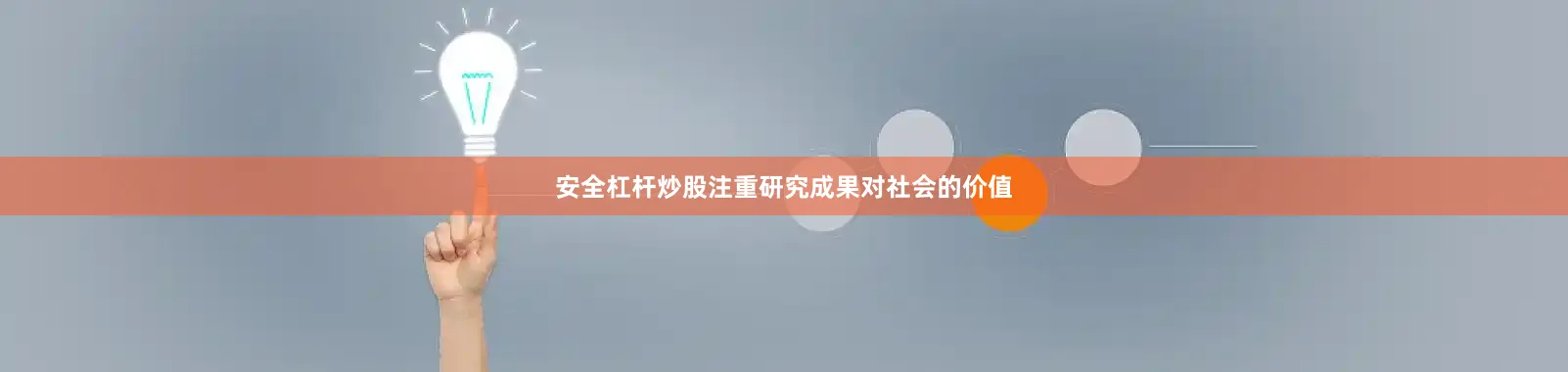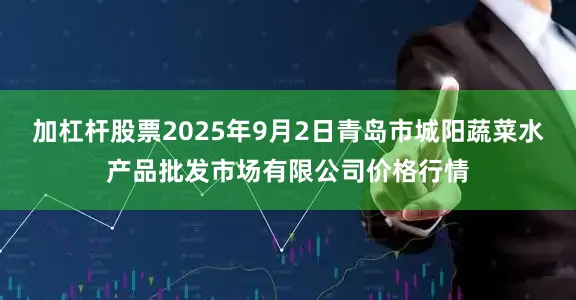创作声明:本文为虚构创作,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,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,仅用于叙事呈现,请知悉。
2000年秋天,上海某医院走廊里突然出现了五个穿军装的男子。
“请问陈德胜老人在哪个病房?”他们神色焦急地询问护士。
当他们出现在病房门口时,齐声喊道:“爸,我们来了!”
所有人都愣住了,这个孤独了半辈子的老人,怎么突然有了五个当军官的“儿子”?
他们到底是谁?
01
那天下午,救护车的尖叫声打破了弄堂的宁静。
陈德胜被抬上担架时,脸色苍白如纸。
“老陈!老陈!”张婶在旁边急得直跺脚。
医生在救护车上忙着给老人吸氧。
“病人有什么病史?”医生问张婶。
张婶摇头:“我也不知道,他平时身体挺好的。”

救护车飞快地开向医院。
陈德胜闭着眼睛,呼吸很重。
到了医院,医生马上把他推进抢救室。
“家属呢?”护士问张婶。
张婶愣了一下:“他没有家属。”
“没有家属?那谁签字?”护士皱起眉头。
张婶着急地说:“我只是邻居,但我可以先签。”
抢救室的红灯亮着。
张婶坐在走廊的椅子上,心里很不安。
她认识陈德胜二十多年了,从来没见过他的家人。
老人一个人住在小房子里,每天买菜做饭。
邻居们都说他是个好人,但为什么不结婚呢?
一个小时后,医生出来了。
“病人暂时脱离危险,但情况还不稳定。”医生说。
张婶松了一口气。
“他需要住院观察,最好能联系到家属。”医生建议。
张婶点头:“我回去帮他收拾东西。”
陈德胜被推进了病房。
他躺在床上,插着氧气管。
旁边的病床住着一个中年男人。
男人看着陈德胜,小声问张婶:“这老爷子真的没有孩子?”
张婶摇头:“住了二十多年邻居,从来没见过。”
“那可真够孤单的。”男人叹气。
第二天早上,陈德胜醒了。
他看到张婶坐在床边,想要说话。
“老陈,你别动,医生说要好好休息。”张婶赶紧按住他。
陈德胜虚弱地说:“谢谢你,张婶。”
“说什么谢啊,邻居就该互相帮忙。”张婶眼里有泪。
护士进来给陈德胜量血压。
“老爷爷,有什么人需要通知吗?”护士温柔地问。
陈德胜摇头:“没有,就我一个人。”
护士看着他,心里有些难受。
这么大年纪的老人,怎么会没有家人呢?
中午的时候,张婶回家给老人煮粥。
陈德胜一个人躺在病床上。
他看着窗外的梧桐叶子慢慢变黄。
手里握着一张照片,是很多年前的黑白照片。
照片上有一群孩子,笑得很开心。
旁边病床的病友问:“老爷子,这是你的孙子们?”
陈德胜没有回答,只是静静地看着照片。
护士小王经过病房,看到这一幕。
她心里想,这个老人一定有故事。
下午,张婶带着粥来了。
“老陈,你先喝点粥。”张婶小心地扶起他。
陈德胜喝了几口粥,精神好了一些。
“张婶,麻烦你了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这话说的,我们是老邻居了。”张婶笑着说。
她心里很想知道老人的过去。
但她不敢多问,怕老人难过。
晚上,陈德胜睡着了。
张婶收拾他的东西时,发现了一个旧铁盒。
盒子锁着,但锁已经很松了。
张婶犹豫了一下,还是打开了盒子。
里面有几封信,信封都发黄了。
张婶拿起一封信,看到地址是军队。
她心里一震,老陈怎么会有军队的信?
其他几封信也都是军队地址。
张婶仔细看了看,信封上写着不同的部队番号。
有海军、空军、陆军的。
这些信到底是什么?
张婶想了很久,决定先不告诉老人。
她把盒子重新锁好,放回原处。
第三天早上,陈德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。
医生说可以下床走动了。
张婶扶着他在走廊里慢慢走。
“老陈,你身体底子不错。”张婶说。
陈德胜点头:“年轻时锻炼得多。”
“你年轻时做什么工作?”张婶试探地问。
陈德胜想了想:“在一家机构工作。”
“什么机构?”张婶追问。
陈德胜没有再说话,只是看着远处。
张婶知道他不想说,就没有再问。
但她心里更好奇了。
中午,张婶回家做饭。
她一直想着那些信件。
最后,她还是决定打电话试试。
她拨通了其中一个地址的电话。
“喂,请问是海军某部吗?”张婶紧张地问。
“是的,您找谁?”对方回答。
“我想问问,你们那里认识陈德胜吗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。
“陈德胜?您是说上海的陈爷爷?”声音突然急切起来。
张婶愣了:“是的,他现在在医院。”
“什么?陈爷爷住院了?严重吗?”对方的声音很着急。
张婶被这反应吓了一跳。
“心脏病,但现在稳定了。”她赶紧说。
“您能告诉我具体是哪个医院吗?我们马上过来。”
张婶报了医院的名字。
“好的,我们立刻出发。请您照顾好陈爷爷。”
电话挂了,张婶呆呆地看着话筒。
老陈到底是什么人?
为什么军人会那么着急?
02
她决定再打几个电话试试。
第二个电话是空军的。
“陈爷爷住院了?我们马上过来!”
第三个电话也是一样的反应。
张婶心里越来越震惊。
这个孤独的老人,竟然有这么多人关心他?
她急忙跑回医院。
陈德胜正在和护士聊天。
“张婶,你回来了。”他看到张婶,笑了笑。
张婶欲言又止,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。
“怎么了?你看起来很紧张。”陈德胜问。
张婶坐下来:“老陈,我有事要跟你说。”
陈德胜看着她,等着她继续说。
“我发现了你的那些信件。”张婶说。
陈德胜的脸色变了。
“我给他们打电话了。”张婶轻声说。
陈德胜闭上了眼睛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“他们要来看你。”张婶说。
陈德胜没有说话,只是握紧了拳头。
过了很久,他才开口:“他们都长大了,有自己的生活。”
“可是他们很关心你。”张婶说。
陈德胜摇头:“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。”
张婶不明白:“他们是你的什么人?”
陈德胜看着窗外,眼里有泪光。
“是一群孩子,我照顾过的孩子。”他慢慢说。
张婶更糊涂了:“什么时候的事?”
陈德胜开始讲起了过去。
1950年代,上海有一家收养机构。
专门收留那些没有父母的孩子。
陈德胜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多年。
他像父亲一样照顾那些孩子。
给他们做饭,陪他们玩耍,教他们读书写字。
“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。”陈德胜说。
“后来他们去哪里了?”张婶问。
“有的参军,有的工作,都有了自己的家。”陈德胜说。
“那你为什么不结婚?”张婶问出了心里的疑问。
陈德胜笑了笑:“照顾他们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。”
“我觉得那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张婶明白了,老人为了那些孩子,放弃了自己的幸福。
“他们现在都有出息了?”张婶问。
陈德胜点头:“每年都会写信报平安。”
“那你应该为他们骄傲。”张婶说。
陈德胜看着手里的照片:“我当然骄傲。”
“这是他们小时候的照片?”张婶问。
陈德胜点头:“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。”
照片上的孩子们笑得很纯真。
张婶看着,心里也很感动。
第四天上午,陈德胜的病情更好了。
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
张婶陪着他在病房里看电视。
忽然,护士小王跑进来。
“陈爷爷,有人来看您。”她说。
陈德胜一愣:“谁?”
护士没有回答,只是说:“您跟我来看看。”
张婶扶着陈德胜走到走廊。
远远地,她看到几个穿军装的人。
他们正在向护士打听什么。
陈德胜看到他们,身体颤抖起来。
张婶扶紧了他。
那几个军人也看到了陈德胜。
他们快步走过来。
陈德胜站在那里,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五个身穿不同军装的中年男子站在走廊里。
他们看到陈德胜,眼里都有泪光。
最前面的海军中校走到陈德胜面前。

其他四个人紧跟在后面。
五个人整齐地站成一排。
然后,他们
同时立正。
齐声喊道:“爸,我们来了!”
走廊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护士们停下了手里的工作。
其他病人和家属都看过来。
张婶张大了嘴巴,说不出话来。
这个孤独的老人,怎么突然有了五个当军官的“儿子”?
他们是谁?
为什么叫陈德胜爸爸?
陈德胜颤抖着手,看着他们。
“志华?天宇?建华?文博?震宇?”他一个个叫着名字。
五个军人都哭了。
“爸,是我们。”海军中校徐志华说。
陈德胜再也站不住了,差点倒下。
几个军人赶紧扶住他。
“爸,您怎么不告诉我们生病了?”空军少校马天宇问。
陈德胜摇头:“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”
“我们是您的儿子,照顾您是应该的。”陆军上尉孙建华说。
围观的人更糊涂了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张婶终于明白了。
这些就是陈德胜照顾过的孩子。
他们长大后都成了军官。
在他们心里,陈德胜就是他们的父亲。
护士小王走过来:“我们回病房说话吧。”
五个军人扶着陈德胜回到病房。
张婶跟在后面,心里很激动。
病房里,五个军人围着陈德胜的床。
徐志华说:“爸,我们接到电话就马上请假过来了。”
马天宇说:“您的身体怎么样?医生怎么说?”
陈德胜看着他们,眼里全是泪水。
“我没事,就是心脏有点问题。”他说。
“我是军医,让我看看。”钱震宇走上前。
他仔细检查了陈德胜的身体。
03
“问题不大,但要好好休养。”钱震宇说。
孙建华问张婶:“您就是给我们打电话的?”
张婶点头:“我是他的邻居。”
“谢谢您照顾我们爸爸。”赵文博感激地说。
张婶连忙摆手:“应该的,应该的。”
陈德胜看着五个孩子,心里又高兴又难受。
“你们都有家有业,不要为我操心。”他说。
“爸,您说什么呢?”徐志华说。
“我们今天能有出息,都是您培养的。”马天宇说。
陈德胜想起他们小时候的样子。
那时候,志华才八岁,是五个孩子中最大的。
天宇只有六岁,总是跟在志华后面。
建华和文博是双胞胎,四岁就来了机构。
震宇最小,才三岁,总是哭鼻子。
“你们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?”陈德胜问。
“当然记得。”志华说。
“您教我们写字,给我们讲故事。”天宇说。
“冬天的时候,您半夜起来给我们盖被子。”建华说。
“我们生病时,您整夜不睡照顾我们。”文博说。
“您省吃俭用给我们买书和文具。”震宇说。
陈德胜听着,泪水止不住地流。
“那些都过去了。”他说。
“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”志华说。
张婶在旁边听着,也忍不住哭了。
她没想到陈德胜做过这么多好事。
“爸,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您生病了?”天宇问。
陈德胜摇头:“我不想影响你们的生活。”
“您是我们最重要的人,怎么会是影响?”建华说。
“是啊,我们每年都想接您过去住。”文博说。
“我在部队给您准备了房间。”震宇说。
陈德胜感动地看着他们。
“我习惯了上海的生活。”他说。
“那我们就经常回来看您。”志华说。
五个人商量着如何照顾陈德胜。
他们决定轮流回来陪他。
每个月都要有人在上海。
陈德胜想阻止,但他们已经决定了。
病房里其他病人都羡慕地看着他们。
“这老爷子真有福气。”有人小声说。
“五个当官的儿子,多令人羡慕。”
张婶纠正说:“他们不是亲生的,是他养大的。”
大家更佩服了。
一个人能把五个孤儿培养成军官,太了不起了。
下午,医生来查房。
看到这么多人,医生很奇怪。
“这都是病人的家属?”医生问。
“是的,这是我们爸爸。”志华回答。
医生点头:“病人恢复得不错,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”
五个军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“爸,我们陪您回家。”天宇说。
陈德胜想了想:“好吧。”
他知道拒绝也没用,这些孩子太孝顺了。
晚上,五个军人轮流照顾陈德胜。
他们给他按摩,陪他聊天。
病房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。
其他病人都很羡慕。
“这样的儿子,比亲生的还要好。”有人说。
张婶也觉得很感动。
她想起自己的儿子,在外地工作,很少回来。
反而是陈德胜这些“儿子”更孝顺。
第二天早上,陈德胜办了出院手续。
五个军人开着军车来接他。
张婶也跟着一起回家。
到了陈德胜的小房子,大家都有些感慨。
房子很简陋,但很干净。
“爸,这房子太小了。”志华说。
“我住习惯了。”陈德胜说。
五个人开始打扫房间。
他们分工合作,很快就把房子收拾得焕然一新。
震宇作为军医,还给陈德胜配了很多药。
“爸,您要按时吃药。”他嘱咐说。
“我们会轮流回来检查的。”建华说。
陈德胜看着他们忙碌的样子,心里很温暖。
中午,天宇去买菜做饭。
他的厨艺很好,做了一桌子菜。
“爸,您多吃点。”文博给陈德胜夹菜。
一家人围坐在小桌子旁,温馨极了。

张婶看着这一幕,心里很感动。
这比血缘关系更珍贵的父子情,让她深受触动。
下午,五个军人要回部队了。
他们不能请太久的假。
“爸,我们一个月后再来看您。”志华说。
“路上小心。”陈德胜叮嘱他们。
五个人依依不舍地告别。
他们约定每周都要打电话。
车开走后,陈德胜站在门口挥手。
张婶陪着他回到房间。
“老陈,你真了不起。”张婶由衷地说。
陈德胜摇头:“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
“能把孤儿培养成这样,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”张婶说。
陈德胜看着桌上的照片,笑了。
从此以后,陈德胜不再孤单。
五个“儿子”经常回来看他。
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来,叫陈德胜爷爷。
邻居们都很羡慕。
“这老爷子真有福气。”
“养了五个好儿子。”
“比亲生的还孝顺。”
陈德胜听到这些话,总是笑而不语。
他知道,当年的选择是对的。
虽然没有结婚,没有自己的孩子。
但他有更多的孩子,更多的爱。
这种爱,比血缘关系更深厚。
春天的时候,志华带着妻子孩子来了。
他们推着陈德胜在公园里散步。
路人看到,都会说:“这老爷子真幸福。”
陈德胜笑着点头。
是的,他很幸福。
74岁的他,终于不再孤单。
他有五个优秀的“儿子”,还有很多“孙子孙女”。
这个大家庭,是他用一生的爱换来的。
夕阳西下,陈德胜坐在轮椅上。
看着远处玩耍的孩子们。
心里充满了满足和安宁。
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。
这就是爱的力量。
配查网-配资股网站-网络配资公司-配资正规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十大平台这可不是随便改改造型
- 下一篇:配资配资网Xbox Series X|S